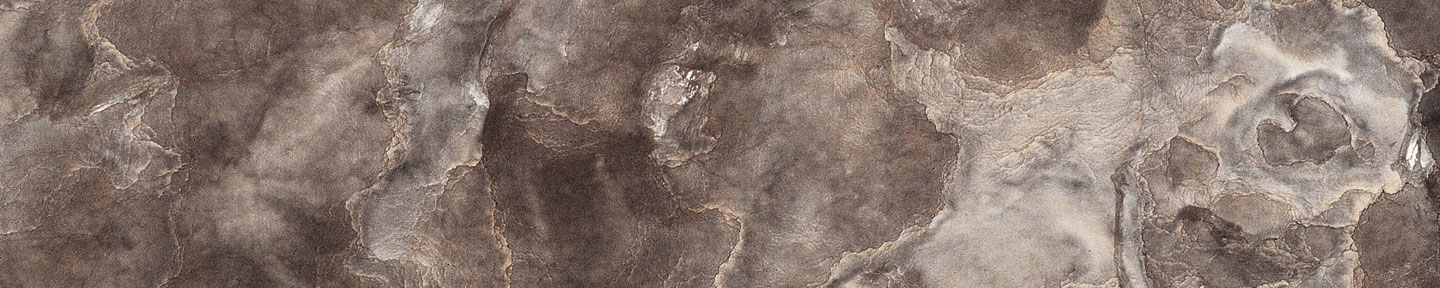【评论】沉默的美学——谈画家晁海之道及其现代水墨之艺
作者:孙金燕 发布时间: 2013-03-22 15:11:38
2010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人物”栏目整版刊登李树森先生对画家晁海的访谈:《开创中国新绘画水墨艺术形态——访著名画家晁海》。该访谈既从文本到人本深刻呈现了“奇人”、“怪人”、“狂人”晁海之种种,又透视出访谈者的艺术情怀与历史担当,读之感触良多。任何大历史都是选“家”史,艺术史也不例外,它需要成熟又有远见的评鉴者,正如艺术品需要灵魂一样。并且,在由对艺术本体的造诣与对文化精神的建构所构成的坐标轴上,艺术史的地标性建筑,总是选择由那些在两个向度上都有突出成就者来承担。被认为“正在开创中国水墨一代宗师的伟业”的画家晁海,或许正在向成为这样一座地标性建筑而崛起,于是,他对文化精神的建构与在艺术本体的造诣,便成为艺术史的执行者们考察的对象。
晁海于1998年始在重要的美术界、博物馆作应邀巡回大型个展11次,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故宫博物院、香港艺术馆、广东省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深圳美术馆等珍藏,并已出版《晁海画集》、《21世纪优秀艺术家——晁海》、《中国当代名家画集•晁海》,得到三十多位国内外著名学者、评论家撰文评论。关于他的种种,甚至被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国际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概括为“晁海现象”。而他的作品,无论是《黄天厚土》、《轮回》、《喘息》,还是《记忆》、《梦回故里》,主要都是“农人”形象或者是以牛为代表的动物形象,且不说这些题材的陈旧与现代艺术界之日新月异之间的格格不入,单说画家晁海能以此获得如此大的殊荣,这其中的落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
为了指正明末清初画坛的摹古之风,清初画家石涛曾提出一个重要的绘画观念——“笔墨当随时代”(《苦瓜和尚话语录》),指认笔墨应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因为语境在发生变化。
确实,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语境,一时代必有一时代之艺术。中国现代水墨的发展也自有其必须面对的语境:其一,从属于渴望突进的精神层面。如同在进化论关照下的“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普遍以《新青年》、《新思潮》等来表达现代性的诉求一样,经历了明末清初至“五四”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的西方文明的冲击,发生于特殊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水墨”,从它命名开始就不曾逃离开它所必须赖以生存的“现代”语境,也不能逃离开这种以“现代”为依托的对于“进化”的渴望。其二,从属于企图消解的物质层面。在经济高速运转的当下,人们已习惯将艺术作为一项产业或商品来经营。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所指称的,作为传统“高雅”艺术准则的独特性、个人性、原初性、本真性、样式和风格等的体现的“光晕”(Aura),使艺术始终建立在仪式的基础上,不管其崇拜的是神奇的对象、宗教的对象还是世俗美的对象。但在机械复制时代,环绕着艺术品的这种神圣“光晕”已经消退,传统美学意义上的艺术品,即作为艺术家个人独特思想与情感表现的结晶,已经为日常大众体验的复制品所取代。艺术品也不再是愉悦感官的美的对象,而已经成为服从者供应与需求关系的一种商品。
这两个不断向上与不断向下的力量之间的牵扯,使中国现代水墨的发展困难重重。自20世纪初便开始的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到80年代初大规模的艺术实验的逐渐开展,表现性水墨、抽象水墨、都市水墨、观念水墨、水墨装置,包括水墨影像等一系列现代水墨实验一路走来,明显在现实依托与形而上追求之间失衡,水墨逐渐成为无法指认的符号与玄而又玄的意义构成,接受者只能牵强附会地认同,革新的路愈走愈逼仄。而无孔不入的现代传媒又推波助澜,在能同步将瞬息万变的世界摆在每个人眼前的幻觉中,强烈甚至是急躁地渴望“提前一步”的艺术,容易在极度的影响焦虑中陷入浮光掠影、空心喧哗、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怪圈。
在艺术的持久性和永恒性精神被一次性、即时性的消费快感所取代的“复制时代”,中国现代水墨也毫不例外地需要承受大众文化或称消费文化的这种以消解艺术的“理想主义”为代价的诱惑。市场操作的介入,“任何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安迪•沃霍)容易使艺术家为机会主义所蒙蔽,失去内心宁静与艺术之坚守,成为非个人(Person)的角色(Persona),在一个交织着商品关系和经济价值的复杂体系内发挥作用。艺术的“光晕”(Aura)消失,“本真性的标准不再适用于艺术生产,艺术的整体功能便被反转。不再基于仪式之上,艺术开始被置于另一种实践之上,那就是政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上世纪90年代轰轰烈烈的“政治波普”和“泼皮现实主义”,即发源于一群秉承自由艺术精神的青年艺术家在艺术的理想主义被消解后的创作。绘画中所加入的****像章、红袖章、五角星、红皮书等,因为携带着特殊的历史记忆,容易被符号化为政治意识形态。“能够将意义掩藏在一个令人误解的符号中,这是语言的独特权力,正如我们将愤怒或憎恨掩藏在微笑背后一样。”(保尔•德•曼:《盲视与洞见》)但问题在于,似乎任何人都断定那种否定性的东西注定要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克服,且欣喜于那种随意、邋遢地摧毁一切所造成的空白性和可操作性,在此情境下,先锋也会急速地流入平面甚至是媚俗。
结果如同阿多诺致本雅明的信中所说的:“先锋派艺术和大众文化都带有资本主义的耻辱伤痕,二者都含有变化的因素,二者都忍痛选择了完整自由的一半,但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完整的自由。”(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新世纪中国画坛的绝大多数水墨革新作品,不仅对水墨画的本体建构缺少必要的关心,即使单就水墨画的精神层面而言,也是既不能提供有关现实的想象,也不能提供有关历史的想象,尽管他们的名利双收,容易让人联想到“德艺双馨”这个词。
艺术一直在召唤能够恪守艺术立场又能积极探索拓展的艺术家的出现。
二
童话《爱丽丝梦游奇遇记》曾呈现一个奇怪的的隐喻:爱丽丝无意中发现一个商店充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但她最古怪的地方在于,每当她使劲盯着其中一个货架,想弄清楚上面到底摆放着什么,那个货架便总是空空如也,而周围的架子却尽其所能地填得满满实实。中国当代画坛也面临着如此诡异的场面:众声喧哗中,可能正隐藏着空空如也的危机。面对精神和历史的深度,操作本身难以成为价值判断,否定艺术深度的空心喧哗,在时间的淘洗中终将难以为继。如此,厚积薄发的画家晁海在水墨画领域的迅速崛起,便不是个值得诧异的现象了。
自上世纪70年代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沉潜二十余年,以创造为己任,殚精竭虑、苦心孤诣钻研探索,旨在寻求中国画之世界性的途径。曾因认为传统中国文人画迫切需要与当代文化精神和历史深处宏大的价值能量相融合,方能承载深厚的历史、彰显其世界性,且立志要完成这一历史性使命,被封为“狂人”;成名十多年却不卖作品,多次婉拒成为签约画家以及拍卖行的参拍邀请,又被授以“怪人”称号。多少年来,晁海似乎已成为一个传说,虚幻的离市场与消费者构成的现实很遥远。
而不论是称其“狂”还是道其“怪”,多少有点价值观反转的意味。其实,画家晁海只是个懂得“沉默”的艺术的人。如他在接受李树森的访谈中所言的:“关于作品卖不卖,是一个有压力的问题。在商业大潮中,外部如此纷扰,自己首先如何处理好与社会、文化信仰和价值及生存等问题,是关键所在,我内心诉求自己适宜回避作坊式的,应具备‘商业返俎’的独特精神,有利于维护自己精神的孤持与静穆的守望”,“在别人不了解我的价值情况下,我也不过多去争论。……正道沧桑。大任和信仰使我更应内敛和包容。”(《著名画家晁海:开创中国新绘画水墨艺术形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2月24日),强烈的历史感与艺术担当,使他有着更强的神经与更高的判断优良的标准,能从喧哗的艺术界的各种物质需求中跳脱出来,并时刻警惕与保持距离。凭借沉默,他解除了自己与这个作为消费者、仲裁者甚至是毁灭者出现的世界的奴役关系。
或者可以说,这种“沉默”是艺术及其所负载的深度意义与艺术家精神气质相契合的结果,“通过艺术,艺术家变得纯净,不仅净化了自己,最终也净化了他的艺术。艺术家(如果不是艺术本身)仍然在追求‘完善’的道路上行进。只不过在以前,他追求的完善控制着他的艺术,而且在艺术中得到实现;对于现在的艺术家而言,最高的完善是达到某一点,在那一点上,出类拔萃的目标从情感和伦理上都不再重要,让他更心满意足的不是在艺术中找到一个声音,而是保持沉默。这个意义上的沉默作为终点,倡导的是一种终极的情绪,它与另一种情绪完全相反,后者告诉人们自觉的艺术家如何在传统的意义上以严肃的态度运用沉默:在这个意义上,沉默是苦思冥想的地带,是思想成熟的萌芽阶段,是最终为言说争取到权利而经受的磨练。”(苏珊•桑塔格:《沉默的美学》)最终,艺术在晁海这里,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白,而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宣泄和苦行实践,并渴望以此进入另一种意义上的“寂照圆融”。
由此,画家晁海能在与市场无关、与体制无涉的状态下,以高度个人化又极为深沉凝重富有文化意蕴的水墨作品,撼动这个时代还未完全丧失的潜在而纯正的审美神经与价值立场。以作品感动所有面对他的人,进入批评的视野,在为市场与体制所役使、为浅近功利所驱迫的画坛,最终以实为正常,却在非正常中显得异常的“异数”姿态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三
保持沉默,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就意味着要比所有人都要技高一筹,否则便会让人指认为内心贫乏而无力表达的懦弱。
画家晁海一直以完成传统中国文人画与当代文化精神和历史深处宏大的价值能量相对接这一历史性使命为己任,而“现代”让传统成为传统,都处在冲突之中,它历来是通过阵痛、裂变而衍生与发展的。他的辨识度很高的现代水墨作品,既不是对传统水墨的以精益求精为过程的死守,也并非以牺牲水墨精神让它成为玄而又玄、难以解读的符号,而是在精神上吸收水墨一以贯之的超越物质,妙在以自然为精神家园的精髓,有机融合世界优秀文化中对人性人本的挖掘,在语言运作上借鉴科学光学领域所带来的色度、色向、解剖等丰富表达,从而突破传统水墨画之创作手法,使最传统的水墨传达最现代的文化精神以及最厚重的历史深度。
晁海是迄今为止唯一不用线而用积墨团块在生宣纸上构建艺术造型的中国水墨画家,他笔下的那些看似发腻的团块所构成的面目模糊甚至有些沉闷的形象,其实正宣示着一种新造的中国绘画语言。如画家晁海自己所言:“这种靠层层积墨而成的言说方式,突破中国文人画鼎新自元明清以来的以点线面、焦黑灰白、干湿浓淡、皴擦点染所产生的视觉节奏与已固秩序,抽离掉传统绘画中被称为‘骨’的线,加强提升墨和笔的内在品质,将原传统墨分五色拓展为无穷无尽的墨色变化,在淡墨和灰墨中寻找有机节奏和韵律,越过难度较小的渴笔点子(即干笔)积或者干湿浓焦、皴擦点染综合式的积墨方法,以润墨在生宣纸上做高难度的层层叠叠的积墨。”这当然必须解决生宣经纬纤维易被墨汁堵死、无气眼的难题,而他的承载在一张薄薄生宣纸上,又层层高出如雕塑般的现代水墨形象的出现,证明他已经寻求到可以打破水墨画创作“一遍活(为泼墨),二遍滞(润墨积),三遍死”的传统积墨手法。并且,这些惚兮恍兮却又历历在目的形象,是对视觉艺术的挑战,更是对传统水墨艺术以及它的欣赏方式的冲击。周秦的古朴恢宏、汉唐的雄浑厚重、宋的极致入微塑造出的“隐”与“空”的气韵,已非教条主义的“阳春白雪”以致“曲高和寡”,而是与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有着“切肤之痛”的凝重。可以说,他独特的积墨手法使其水墨画抵达的精神厚重感,是以传统绘画语言运作方式所不能完成的,并且也是仅靠其表现的对象或者称为内容所无法独立呈现的,尽管作为千年农业大国,农民形象与牛的形象本身已负载极为丰厚的历史深度。或者可以说,画家晁海之所以能逃避开喧嚣以选择“沉默”,是在对东西方艺术深刻求索后的艰难抉择。他有自己确认的标准,以及以此判断出自己必将呈现的历史价值,在难以被落后一步的社会价值判断认同时,他的傲骨其实只有一个出口了,这个出口便是以一种对历史对艺术的热情、担当甚至是悲悯情怀,突破以往无人突破的至难之境,创造出纯然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独特的艺术新语言与新精神,进而展开对人与宇宙的恢宏、厚重的精神力量的充分挖掘。经过多年在“沉默”中的探索与实践,他已经站在这个“出口”准备会心一笑了。
结语
笔墨之道,本乎性情,一旦我们以自身的修为达到能更好地阐释自己、阐释世界的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世界对我们而言也就有了全新的意义。作为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从小生活在农村的画家晁海,乡间劳动者的勤劳、善良、朴实的美德以及默默承受的顽强生存意识,使其对勤劳的耕耘者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其素材中的农人形象以及牛的形象,主要也在为了呈现逆境中顽强地承受和生存的价值核心。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为它们寻找到了一条更为现代也更为厚实与坚挺的呈现途径,从而引发对于水墨、对于艺术甚至是对于人生的更为切实的思考。
事实上,在关于艺术表层化的喧哗之后,中国艺术正在直截了当地仿制、复写与固守内心的体验,深省之间彷徨。在自觉远离浮躁的假面狂欢时,“沉默”为画家晁海思想的延续或深化赢得时间,也促使或帮助其语言获取最大的完整性或严肃性。至道无难,惟嫌拣择。无论是不可拣择,只能面对的无奈,还是不愿拣择,甘心面对的悲悯,只有“沉默”以进方才能抵达“至道”,这对于艺术家本人甚至是艺术本身,其实都是如此。
2010年3月写于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