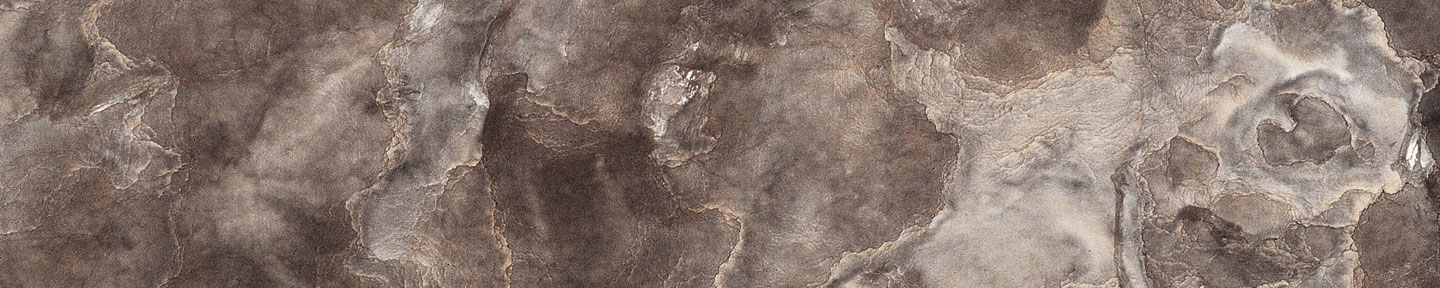【观点】坚守与远离
作者:胡仰曦 发布时间: 2013-10-08 16:47:31

本刊特约记者梁存收与知名画家晁海(左)合影
时间:2013年7月20日下午
地点:西安某酒店
受访者:晁海知名画家
采访者:梁存收《传记文学》杂志社特约记者
梁存收(以下简称梁):晁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传记文学》杂志杜的采访。大家知道,您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这个年代的人的心灵深处总会承载着或多或少的挥之不去的“灰色记忆”——“三年自然灾害”、“**”,这些人生的阅历是否会影响您后来的创作或者对绘画语言探索的思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晁海(以下简称晁):“三年自然灾害”始于我幼年时期,这对于我后来艺术的发展与成长难免会产生一些忧患意识。自然我也会对土地、劳作者、庄稼有一种很深的情感,而且也会影响到我后来的艺术观点,苏东坡有诗曰:“秀句出寒饿”,不少好的艺术作品来自艰苦的环境。幼年的饥饿记忆它会时时的催促我要奋发,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对这种生命的追求可能就没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就没有对土地、对劳作者、对粒粒皆辛苦的一种珍稀记忆。我觉得艺术家受到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影响后,会激发他内在的一种感受,当然这也会使我对这种悲剧的艺术、悲剧的绘画有一种本能的关注,因为在这种悲剧的绘画中有一种悲壮的、深刻的美,这和我绘画表现的题材有一定的联系。
“**”十年**,使中国人的精神很虚妄,作为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正处在少年初期。当时的我就感觉很困惑也很纠结,很多人、很多家庭为了观点不同、追求真理而分道扬镳,因观点不同互相之间的“武斗”,“**”使我感受到是一种人性长期压抑后的集中爆发,这种释放口是否正确它也无所顾忌。这对我的绘画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它让我思考并对人性进行反思……也让我意识到应该对社会有一种清醒的剖析,以此体现在我的艺术创作之中。总之,“三年自然灾害”和“**”对我以后的艺术的创作中对那悲悯的情怀,以及对我作品深沉的表达是一种催化。
梁:1977年恢复高考后,您考取了西安美院系统接受学院派的教育,是什么样的环境或者动力敦促您做出该选择?这种学院派的教育对您后来的艺术探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晁:因为家父是一位秦腔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武术家,他对儒、释、道中国的主体文化,以及古典的人文有自己很深的感情和体验,经常在我幼时、练功的时候熏陶我,所以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也许是一种家族式的渊源继承吧。小时候父亲从北莽塬坡挖几块黄土背回家,泡在盆里催我写黄泥大字、画画,并加以启发与鼓励。所以我后来的艺术创作和报考艺术类院校的机遇与家父对我的引导有很大的关系。还有我在初中、高中办黑板报、画宣传栏,在县文化馆画画就受到大家的关注,受到一致好评。这样自己就觉得应该上美术学院,立志成为一个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画家。
学院派的教育自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两大块,一个就是西欧体系,一个就是前苏联的体系,这两个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学院派的主流体系。它是解决形、光、色、体积、量感的一种技术,它是西方用科学分析事物本身的一种方法,训练我们有秩序地去分析物象并表达对象的质感、量感、空间感,在艺术上表达着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对我个人而言是发展我以后形而上的艺术语言不可或缺的训练。比如石膏像在受光下,它的色阶、色度无穷变化,这种理性分析和感悟对象的方法运用在水墨积墨法上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墨色体积、厚度变化。
梁:在1998年之前的15年期间,您一直潜心研究绘画的语言,探索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风格样式,15年的坚持,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或者精神在支持您,如痴、如醉?这其中的辛酸与痛苦,喜悦与欢笑能否与我们分享?
晁:1998年前的这15年期间,我一直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国际上的位置,已经想改变它的尴尬境地。但在现实的国画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保留文人画的精髓,但缺失了担当和悲悯,有了普世、济世的情怀又没有了文人画的精髓。文人的精髓就是纯粹性、超越现实、无烟火气,但是要表现真实生活,文人画的精髓又丢了。所以我要做个大的课题,研究学科前沿,研究这种绘画的语言形态,既有悲悯、担当又有文人高雅的笔墨纯粹性,这两者的结合是矛盾的,它们的结合非常难,就像一个修长的跳高运动员要举起重磅杠铃,而粗壮身板的举重运动员要越过跳高运动员的高度。所以刘骁纯先生说:“变雄浑为淡泊”,这个雄浑里头既要直面我们沉重的生活又要和周秦汉唐厚重积淀相结合,淡泊是指的文人表现的空灵、超凡、虚无与文人的庄禅哲学,那么这个课题就敦促我要坚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85年我母亲突然患上了脑血栓,对我打击很大,没有照顾好老母亲,心里很内疚,但这越发使我感觉担子的沉重,要完成这个课题的时间紧迫性。当时学校住房紧张,我一直住在基本废弃的老美院,夏天漏雨,一会儿这边漏,我把画案挪过去,那边又漏我再挪回来,上个厕所要用个棍子拨开草丛到山上去。冬天要捂住鼻子画画,为什么呢?因为怕清鼻涕滴到宣纸上……这个艰难的过程对于意志力是个考验,我要照顾母亲又要完成这个课题,两边都要顾及,这其中的艰辛是很难表达的。
梁:您曾经把自己的人生规划为三个阶段:以创造(其中闭门15年)、传播(已15年)为己任,精神价值转化为物质价值,完善民族水墨文化价值体系。您认为传播阶段是个艰辛的过程,那么传播阶段是否应有个时间节点呢?您认为精神价值转化为物质价值所必备的因素是什么?
晁:在第一个15年(1983年至1998年)间,我殚精竭虑、卧薪尝胆,潜心研究上面所说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很大,也没有精力传播,别人不理解,人不知而不愠。但当研究到一定程度,并具有国内外前沿的高度和广度,画面语言给人产生最可贵的陌生化的时候,别人不理解甚至排斥的时候,沟通、交流、传播才显示出其重要性。当然这个交流、传播的方式就是在国家重要的美术馆、博物馆做个展,个展之余也有私下的探讨与交流。传播和创造同等重要,你没有创造就没有传播,有些人只有传播没有创造那就缺乏学术性,没有学术性、精神性的支撑那艺术的生命就是短暂的。关于传播时间的节点,我认为作为一个水墨艺术的践行者是应该没有一个具体限定的节点,它和创造是并行的,随着创造的进一步深化传播的深度也会有所推进。
精神价值转化为物质价值也就是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它所必备的因素应有背后的文化支撑、精神支撑、学术支撑,只有具备这些,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后才持久,没有精神性、学术性而只有市场我认为也是不长久的。对我而言要进入更大的市场,需要几个方面:第一,要挖掘文人画的精髓。第二,是挖掘周秦汉唐鼎盛时期的恢弘和博大凝重的气魄。第三,就是挖掘东方远古神秘的哲学观,从自然观和天人合一的观点看待事物。第四,就是研究、学习西方的哲学、教堂、建筑、雕塑,因为这些是西方审美文化的积淀。第五,就是深化学院派的教育,它是艺术的造型支撑,它形体的严谨与中国哲学形而上的结合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五块的有机结合才能在市场上经久不衰。
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您出生在悲壮的西北黄土高原,又有璀璨的古长安文化的孕育,这是否是造就您的绘画作.品具有汉唐深沉雄大的原因?在您的作品中能读到一种凄凉和苦涩、悲壮与苍凉,您能否给我们分享下您的创作缘由和题材的出处?
晁:这是肯定的,陕西西安曾拥有周秦汉唐13个古都,反映了周秦汉唐博大精深的文化氛围,也造就了西安这个地方的文化意蕴。这种文化就像黄土高原西北的一种植物叫柠条,风沙把它覆盖在6米厚的沙土里面,它都能长出来,每长出1米它的根就向两边延伸吸取养分,据植物学家考证最长能延伸12米,这种情况下外界的狂风是很难把它吹走的。西北的植物在荒寒、苦涩的环境中保持着一种生命的状态,在艰难的环境中体现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西北人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类似的精神,是环境给他们的滋养和熏陶。在这种环境下才能产生出悲壮的美、震撼心灵的美。
我的家乡在关中平原,20世纪60年代,冬天的耕牛由于缺少相应的草料瘦骨嶙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让其继续劳作并繁衍后代。有时牛累了卧在地里站不起来,经常会出现抬牛的场景……这些使我对画面感有独特的个人体验,这也是在我后期的绘画创作中艺术灵感的源泉。还有就是麦子熟的时候会采一批甘肃麦客,他们翻山越岭跨越几个省不断地割,他们的勤劳和辛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的艺术作品当中产生了一种苍凉和苦涩的美感。所以很多人说我的作品具有灵魂体验,具有悲壮的美,这种美是劳苦大众用血汗换来的。
梁:您经常引用古人:“天地之包容,宇宙之沉默,方后可为仁”这句话,它体现了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美学意蕴,彰显了对人生观、世界观的深层思考,这在您的绘画作品中也有所。凸显。您能否结合您的作品谈谈您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认认知和解读?
晁: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应该反映出很多内在的东西,尤其在国画中应有中国哲学思想内涵,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含蓄、内敛、包容和厚重,比如我们在作品中要表现一头牛,这头牛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牛,它仅是生活中牛的载体,关键是能折射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可谓图腾。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我用积墨把这头牛和劳作者的精神状态表现出亘古苍茫感,似牛非牛,牛之化石,从远古走到了今天,这是厚重和内敛的结合,并且具有一种包容性。我在做研究绘画语言课题的时候要保持一种沉默,不与人争辩,不要计较暂时的得失,要沉住气,也要有包容性。中国远古哲学有一种混沌境界,它既有又无,既无又有,它是包容世界万物的一种哲学思考。这种思想反应到生宣纸上时,用墨非常淡但是很厚重,非常虚幻但是物象的肌理清晰可辨,能体现出青铜器、石刻、雕塑和化石的纹理和性格,我觉得这就反映出一种中国哲学的精神,乍一看画面是虚幻的,但同时又有极强的三维立体空间感。
梁:大家知道您是习武之人,习武与绘画创作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样东西,而它们都经过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洗礼,成为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瑰宝,在您多年的实践中您认为它们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习武对您的绘画创作是否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晁:习武对我的绘画来说有一种非常积极的影响。中国的武学文化也是来自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的武术不但是体能性的,还是一种精神性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比如说“瞳子观背、耳朵听内、浑身放松、血脉畅通”,“空手拿木剑、倒打紫金冠”等,都具有一种精神性的、哲理性的思考。从这些武学深厚的内涵中我悟得很多与绘画相同的中国文化精神,并应用于我的积墨绘画领域。
我认为武术的这种物理属性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精神性了,这种精神性跟我们的绘画的精神性是一致的,也就是人的智慧、意志、信念的集中体现,他们之间有一种通感。我在表现画面的时候不用中西融合体系中的明、暗、交界线表达立体,而用阴阳、感应互动表现具有岩石般的肌理和苍茫,用一种形而上的感应来表现具体的画面,它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它是在中国薄薄的生宣纸上表现立体的物象,而有别于西方的形、光、色体积的表现。
梁:众多评论家曾以“厚重’’、‘‘雄浑’’、‘‘深沉’’、‘‘朴实’’等来评价您的作品,这其实是您画面传达给他们的一种精神解读,然而承载这种精神的要素一是需要题材,二就是需要技法。尤其是您独特的“积墨法”令很多人折服,达到了开宗立派的境界,您能否具体地谈谈您的“积墨法”?
晁:我的积墨是用淡墨积,而非渴笔点子积,也非干、湿、浓、淡、皴、擦、点、染综合式的积,常言道:润墨泼一遍活、二遍滞、三遍死。因为生宣的经纬纤维易被墨汁堵死,无气眼,这是一个很难突破的至难之境。所以我选择淡墨并以内在的感应力、恒力、意志力数十遍、几十遍、—上百遍的积,一张画要画一个月、二个月甚至半年,这样的画面语言就很含蓄也很震撼、生动,在粗犷中表现庄重,内敛中表现它的雄浑。
在用墨上也要非常讲究,要用研的墨,研得很细的墨来入画,如果墨粒太大就会堵住宣纸的气眼,积不了几遍就死了。
我的积墨法不用线而用隐态笔、墨层层积,在积的过程中把握它的节奏和韵律,在纯粹中寻找变化,在变化中寻找历史文化的积淀。
梁: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您的绘画艺术是一种中国本土视觉语言,然而由于您的创造、革新与探索冲破了传统水墨画的囿限,摆脱了传统文人笔墨的成规,而着眼于国际视野,您的艺术品格已经具有一种“国际范儿”,对于这种放眼国际的胸怀和魄力,您是否认为是艺术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呢?
晁:我认为放眼世界是每位艺术工作者应该担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当前,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领域里面处于一种尴尬的境界,我为什么做这个课题呢?我做这个课题的意义就在于,想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文化具有创造的潜能和智慧。我们的传统哲学思想、传统文化精神、世界优秀文化以及当代人的感情思想的结合足以产生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水墨艺术,因为我们具备这些文化的基因和信息,只不过是对于意志力的挖掘和信念的坚持不够。我生活在地域特殊的西安又有学院派的教育,加之我对传统文人画、西方绘画、西方经典哲学的研究,这又赋予我创作的信念。我们以民族为根基、为主体,建构具有国际性的新的艺术形态。
梁:在物欲横飞的当今社会,您却能独善其身坚守自己的绘画阵地,远离书画市场的各类诱惑,这也是您练内力的一种方式,请您谈谈关于当今书画市场的看法以及您的艺术作品进入到市场的时机。
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宏观和实践的把握至关重要。针对艺术品进入市场首先要看是否对精神性和艺术性价值有所承载,其次要有重要美术馆、博物馆的收藏,这是前期的功课。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前它必须具有文化含量、艺术含量和精神含量。对于中国画来说,作品吸收传统文人画的笔墨精髓如何?文人笔墨是中国画的核心价值体系。现在的书画市场整体来看没有宏观意识,没有微观扎实,缺乏忧患意识,只是一味地获取物质,缺少精神的追求和绘画语言的探索,这就造成大量的应酬之作泛滥。这样的艺术道路向前怎么走?是非常尴尬的,应该理性的回归。
2010年我的绘画作品在保利拍卖,这个时间我感觉是比较合适的时机,因为我从1983年开始到1998年15年期间做课题研究,自1998年开始我就开始巡回展,在上海、香港、广东、北京、浙江、南京、深圳等地一共做过巡回展12次,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水墨艺术作品。我在1998年出了第一本画册,打开画册后看到是浓郁的东方神秘文化和西方浓郁的宗教气息,混沌、鸿蒙、潜隐,恍惚有像、有形……这是艺术精神的需要。再深入看有没有当代人的感情体验,它有没有用形象表达形而上的意念,有没有普世、济世的理念。整体上来说我的作品呈现的面貌是一种混沌状态,能让人产生一种陌生感,但是懂者深谙其中的内涵玄机。在这一阶段中我回避卖画,而在这集中传播后,2010年我认为时机成熟了。
梁:您作品传达出的视觉张力令人感动和震撼,并形成了自己的个人风格,然而这种视觉意识的形成需要艺术家耐住寂寞、苦心探索,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于今天的画面语言您是否已经满意?或存在哪些忧虑?您是否还要进行下一步的探索?
晁:我对自己的水墨艺术喜忧参半吧。因为我的性格和理想决定了我对我的绘画追求的不满足,但令我欣慰的是通过我的努力,完成了五大创化观(见后面文章),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认同。《世界艺术论坛》六整版报道我的艺术历程和绘画成就。但我的担心也接着来了,怕各种其他事务占据我的创作时间,再一个就是我的颈椎出了点问题,有一次吃饭,碗从手里掉下来了,这使我也很担心。作为一个探索型的画家本来作品就少,再加上身体的原因使我出现了一些忧虑。
我个人还是痴迷对艺术的追求,尤其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精神追求。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它有很强大的包容性和精神性,元明清及近代的文人画已成固有秩序和法则。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突破很难,它们超凡脱俗的美感、纯粹感,浓、淡、干、湿的用笔是很难超越的。但要从这里面走出来有所创新让西方人看到中国文化的再生性,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信念。
关于下一步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梁:非常感谢晁老师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接受《传记文学》的采访,今天您从不同的角度对您艺术成长历程进行了剖析和解读,这对我们了解您画面的语言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能让读者从全新的视角了解了您的创作思想。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对您进行采访。
责任编辑/胡仰曦